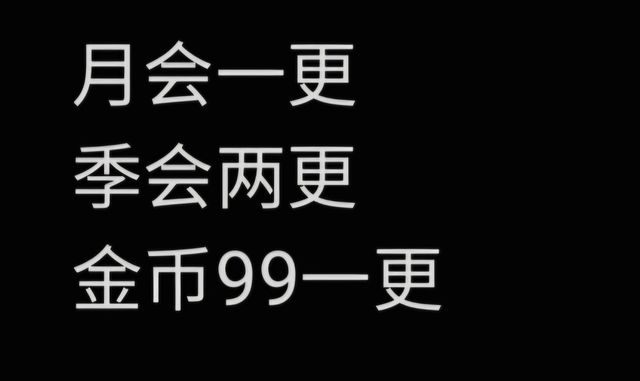(接上文)
日本兵的刺刀抵在我腰间,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金属的寒意透过衣料。报社的旋转门近在咫尺,却仿佛隔着一整个世界。身后传来押送士兵的嗤笑:"支那女人,算你走运。"
推开门的那一刻,同事们的目光像聚光灯般打在我身上。我的衬衫领口撕裂了一道口子,裙摆沾满羁押所的泥污,指甲缝里还留着挣扎时抠下的铁锈。老张手里的茶杯"啪"地掉在地上,茶水溅湿了我的鞋尖。
"清月!"
叶冲的声音从门口炸响。他喘得厉害,西装领带歪斜着,向来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垂了几缕在额前。我从未见过他这般失态的模样。
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,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。直到坐进车里,他才松开手,方向盘上立刻浮现出五个清晰的指印。
"没事了,我会想办法的。"他重复着,声音轻得像在安抚受惊的动物。后视镜里,我看见自己的眼睛——空洞、干涸,像是被掏空的井。
叶公馆的壁灯将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,扭曲成奇怪的形状。我盯着茶几上那杯热茶,水面不断震颤,才意识到是自己的手在发抖。
"他们只是想喝口水...都不给..."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。
茶杯突然炸裂,滚烫的茶水溅在我的手背上。我竟感觉不到疼。叶冲半跪在我面前,用帕子一点点擦去我手上的茶叶,他的睫毛在灯光下投下一片阴影。
"那些被带走的人...会怎么样?"我抓住叶冲的衣领,布料在指间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。
叶冲的瞳孔收缩了一下。这个微小的反应像刀一样刺进我心里——他知道答案,而那答案比死亡更可怕。
我的哭声撕碎了夜晚的宁静。叶冲把我按进怀里,他的心跳声震耳欲聋。隔着西装面料,我咬住他的肩膀,直到尝到血腥味。他没有动,只是收紧了手臂,像要把我揉进骨血里。
连续三天,叶公馆成了镀金的囚笼。每天清晨,叶冲都会在玄关停留很久,目光扫过每一个可能藏匿危险的角度。今天他回来时,身上带着浓重的烟味——他向来克制,除非遇到极棘手的事。
"佐藤要办酒会。"他解开领带,动作有些粗暴,"点名要带何樱。"
窗外的玉兰树沙沙作响。我想起何樱别在衣领的珍珠胸针,在阳光下闪烁的样子。"她能应付,"我说,"她比我们想象的更坚强。"
叶冲突然转身,手指抚过我的眼下——那里有连续失眠留下的青黑。"明天...我该回报社了。"我抓住他的手腕,他的脉搏在我掌心跳动,"总不能躲一辈子。"
月光透过纱帘,在他脸上织出细密的网。我们沉默地对视,某种无言的约定在空气中凝结。最终他叹了口气,额头抵上我的:"至少让我送你。"
报社的玻璃门反射着夕阳,像一块凝固的血。我刚踏出门槛,就嗅到了那股熟悉的古龙水味——混合着枪油与野心的气息。
"江记者。"宫本从阴影中走出,军靴锃亮得能照出我僵硬的表情,"气色比上次好多了。"
我径直走过他身边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他突然横跨一步,制服上的金属纽扣硌得我手臂生疼。
"还在为那些蝼蚁生气?"他俯身在我耳边低语,呼吸喷在颈侧,"你应该感谢我,如果不是我恰好巡视..."
"感谢?"我猛地抬头,看见他眼中戏谑的光,"要不要我替羁押所的那些人给你也道个谢?"
宫本的表情瞬间阴鸷。他一把扣住我的下巴,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颌骨:"江清月,你该学学怎么当个聪明的女人。"拇指粗暴地擦过我的嘴唇,"明晚的酒会,七点我来接你。"
他松开手,我的后背已经抵上冰冷的砖墙。远处传来日本军车的轰鸣声,像饥饿的野兽在咆哮。宫本倒退着走入暮色,嘴角挂着势在必得的笑:"记得穿漂亮点,我讨厌苍白的花朵。"
(未完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