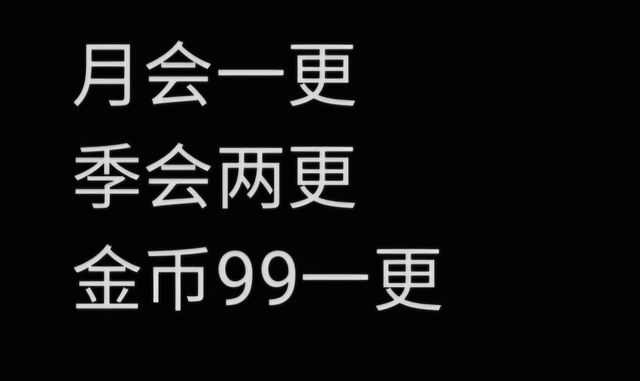(接上文)
夜色如墨,叶公馆的花园里弥漫着夜来香的馥郁。清泉纯子站在廊下,指尖划过一朵盛放的玫瑰,花瓣在她手中碎裂,汁液染红了指甲。
"我不在的这三年,冲哥身边多了好多人。"她盯着正在修剪花枝的何樱,声音比夜露还要冰凉。
叶冲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,纯子转身时已换上甜美的笑容。离开时,她的目光掠过玄关处的合影——照片里三个孩子笑容灿烂,可镜框边缘已经泛黄。指尖轻轻擦过玻璃表面,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。
"感情...也会像照片一样褪色吗?"这句日语低语消散在夜风中。
客厅里,何樱将一束白菊插入青瓷瓶,水珠顺着茎秆滑落。"今天见到清月了吗?"她突然问道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花瓣。
叶冲的茶杯停在半空,茶水映出他微微蹙起的眉头。
"上午她来学校看我,送了这枚胸针。"何樱碰了碰衣领上的珍珠藤蔓,银光在灯下流转,"下午说有约就走了...你们是不是..."
"她去找小庄了。"叶冲放下茶杯,瓷器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何樱忽然攥紧了手中的花枝,荆棘刺入掌心却浑然不觉:"叶冲,清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做了很多。"她的声音轻得像叹息,"上次假余教授的事,学校撤离的事...她明明和我们差不多大,眼睛里却总是藏着我看不懂的东西。"
月光透过窗棂,将何樱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她接过叶冲手中的剪刀,刀刃反射的冷光划过两人之间:"那个笑得那么明亮的姑娘,其实背地里哭过很多次吧?"
剪刀合拢的声响中,叶冲的回应几乎微不可闻:"...我知道。"
香港的街头弥漫着硝烟的气息。我贴着墙根疾走,掌心全是冷汗。转角处突然传来皮靴踏地的声响,我还没来得及躲藏,就被两个日本兵架住了胳膊。
"放开!我是大公报记者!"我的抗议淹没在刺耳的哨声中。
羁押所的铁门在身后重重关闭,血腥味混着排泄物的恶臭扑面而来。昏暗的仓库里挤满了人,有人蜷缩在角落呻吟,有人呆滞地望着高窗外的一线天空。一个约莫六七岁的孩子趴在母亲膝头,干裂的嘴唇蠕动着:"妈妈,我渴..."
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推开拦路的士兵,我冲向那个佩戴少尉肩章的男人:"给他们水!至少给孩子水!"
对方狞笑着扬起手,我眼前一黑,整个人摔在潮湿的水泥地上。耳畔嗡嗡作响,视线模糊中看到周围日本兵笑得扭曲的脸,他们锃亮的皮靴围成一圈,像某种嗜血的兽群。
"江记者?"宫本的声音从高处落下。他蹲下身,手套白得刺眼,"真是狼狈啊。"
我拍开他伸来的手,血从嘴角渗出来,在衣服前襟绽开暗红的花。身后传来压抑的啜泣声,那个要水喝的孩子正被母亲死死捂着眼睛。
"放他们走。"我撑着墙站起来,铁锈味在口腔蔓延,"他们做错了什么?"
宫本整理着手套,嘴角挂着礼貌的微笑:"大东亚共荣需要牺牲。"他突然用日语厉声呵斥,士兵们立刻立正站好。
当两个士兵架起我时,仓库深处突然爆发哭喊。一个老人扑向铁门,又被枪托砸倒在地。血从他花白的鬓角流下,在肮脏的地面画出蜿蜒的红线。
"宫本苍野!"我的尖叫撕破空气,"你看看他们!那些孩子可能再也见不到父母,那些老人会死在异乡!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共荣?"
宫本的眼神终于出现裂痕,他粗暴地拽住我的手腕:"江记者,有些问题你不该问。"
被拖出大门时,我最后回头望去。夕阳透过高窗,将铁栏杆的影子烙在每一张绝望的脸上。那个要水喝的孩子趴在铁栏前,脏兮兮的小手徒劳地伸向光明——
我好像看到了1937年的金陵城。
雨水突然倾盆而下,冲刷着我脸上的血迹。在囚车轰鸣的引擎声中,我听见自己在哭,可眼泪很快就被雨水吞没。香港的天空依旧蔚蓝,可我们的明天,究竟被带去了何方?
(未完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