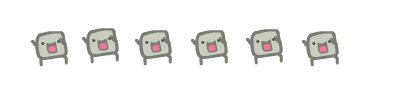深秋的雨丝如银针般穿透H市老旧的梧桐叶,在青石板路上洇开深浅不一的水痕。朱志鑫蹲在巷口的警戒线内,他身形颀长,却因长期伏案显得有些单薄,藏青色警服被雨水浸得发沉,却依旧熨帖地勾勒出窄腰线条。他微垂的侧脸在雨幕中显得格外苍白,下颌线绷得极紧,几缕被雨水打湿的黑发黏在饱满的额角,露出眉骨高耸的轮廓——那是双极其锐利的眼睛,瞳仁是深不见底的墨色,此刻正专注地盯着死者指缝,长睫上凝着的雨珠随眼睑颤动,像未落的泪。
指尖捏着镊子的关节泛白,指腹常年握枪磨出的薄茧蹭过不锈钢器械,夹起一缕蓝色纤维时,他腕骨处的青筋在苍白皮肤下若隐若现。这双手本该更适合握笔,而非警械,指节间却带着常年训练留下的冷硬弧度。
“警察哥哥,这个可以给我看看吗?”
少年的声音像含着蜜糖,撞进朱志鑫冷冽的思绪。他回头时,雨水恰好从帽檐滴落,划过他挺直的鼻梁,在唇峰留下一道水痕。眼前的明黄色身影与他周身的冷色调形成刺眼对比——及腰的白发用向日葵发绳束在脑后,而他自己的头发不过及耳,被警帽压得服帖,唯有鬓角几缕倔强地翘起,沾着泥点。
“这里禁止入内。”朱志鑫站起身,警靴碾过碎石的声响在空巷回荡。也许是他天生的身体问题,导致这个看起来比他小的少年居然比他高出一个头有余,肩宽撑得警服肩部线条格外利落,只是转身时,袖口不经意露出内侧医用胶布的痕迹——那是今早例行抽血留下的。他注意到少年连帽衫边缘的暗红污渍,眼神瞬间沉下来,眉峰蹙起的弧度像把冷刃:“你什么时候来的?”
少年忽然笑起来,露出尖尖虎牙,而朱志鑫的唇始终抿成一条直线,只有在思考时,下唇会被犬齿轻轻咬住。他看着少年手腕上的月牙疤痕,下意识摸了摸自己后颈——那里藏着道更浅的疤,好像是幼时被父亲强制参加体能训练时摔的。。。
“别碰。”他抓住少年手腕的瞬间,两人的手形成鲜明对比:他的手掌宽大,指腹粗糙,虎口处有常年握枪的厚茧;而苏新皓的手纤细白皙,指尖甚至带着画室特有的颜料薄痂。体温的差异让他指尖一颤,这才发现自己的手确实如少年所说,凉得像冰。
法医车鸣笛时,朱志鑫望着少年跑远的明黄色背影,忽然注意到自己警服第二颗纽扣松了线头——那是今早出门前,母亲不满地扯过他的衣襟时拽的。他低头整理领口,喉结在苍白皮肤下滚动,雨水顺着下颌线滑落,滴在胸前警徽上,映出他自己那双写满疲惫与疏离的眼睛。
当他捡起泥地里的银质袖扣,指腹擦过鸢尾花纹路时,袖口露出的医用胶布被雨水泡得发白。远处白鸦嘶鸣,他抬起头,雨水模糊了视线,却清晰地看见自己映在水洼里的倒影:肩背微驼,眼神冷硬,唯有紧攥袖扣的手指,泄露了一丝不为人知的颤抖。
“队长,死者身份确认了……”
助理的声音传来,朱志鑫接过照片的瞬间,指节因用力而泛青。照片上的白发与向日葵发绳刺痛了他的眼,他忽然想起少年仰头对他笑时,发梢扫过他手背的触感——像一片羽毛,却在他心上划开了道看不见的口子。
巷口的风卷起他的警服下摆,露出内里苍白的脚踝。他望着少年消失的方向,那里此刻只有被雨水打落的梧桐叶,和一枚卡在砖缝里的向日葵花瓣。而他自己,不过是这阴雨天里,另一株无法向阳的植物,只能在警戒线后,用冷硬的外壳包裹住随时可能碎裂的内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