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丝敲打着伊波特山的岩壁,将“登山者有去无回”的古老传说泡得潮湿而粘稠。当第一缕梦魇的诅咒如雾气般渗透进城市的霓虹,地表世界的崩塌便进入了不可逆的倒计时——48小时,足以让后工业文明的喧嚣沦为绝望的哀鸣。
城市是诅咒蔓延的绝佳温床。夜幕降临时,梦境病毒已悄无声息地侵入了千万人的潜意识:上班族在梦中看见自己的电脑屏幕渗出黑色粘液,学生在课桌前被同学空洞的眼神包围,医生的手术台变成了扭曲的祭坛。当黎明刺破天际,感染的人们从睡梦中醒来,瞳孔里只剩混沌的灰白,无痛觉、无理智,仅凭本能追逐着未被感染的生命。他们的指尖滴落的黑色液体,接触到皮肤便会留下灼烧般的纹路,短短十分钟就会完成感染闭环。密集的社区成为变异体的狩猎场,公寓楼的楼梯间回荡着拖拽声,超市的货架后藏着喘息的幸存者,原本象征秩序的街道被失控的汽车堵得水泄不通,那些被感染的机械无需燃油,引擎嘶吼着撞向一切移动的目标。
人类的反抗在诅咒面前不堪一击。尽管人类的决心天生强于怪物,但绝大多数人无法像Frisk那样掌控这份力量,微弱的抗性只能延缓感染几小时,最终还是会被黑暗吞噬。枪械射出的子弹能击碎变异体的躯体,却无法阻止其残骸重新拼接,反而会让开枪者瞬间被诅咒反噬——击杀感染者的强制感染机制,让每一次暴力反抗都变成自我毁灭。医院的实验室里,医生们对着显微镜下不断变异的病毒束手无策,现代医疗仪器连诅咒的本质都无法解析;网络信号没有成为求救的桥梁,反而沦为幻境传播的载体,未感染人群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亲人求救画面,全是引诱他们走出避难所的陷阱。
感染源的多元化让灾难雪上加霜。农田里的农作物脱离了阳光与水分的依赖,疯长的藤蔓缠绕着村庄,花粉中裹挟的病毒随风飘散,吸入者会立刻陷入意识模糊;森林里的树木长出了漆黑的叶片,枝头悬挂的不是果实,而是被感染后僵化的动物尸体,它们会在猎物靠近时突然坠落,用利爪撕扯一切活物;就连河流中的塑料垃圾、废弃金属,都被诅咒激活成了移动的杀戮机器,顺着水流漂向伊波特山的方向,成为连接地表与地底的“感染桥梁”。更致命的是六个人类灵魂的原主人遗物——那些散落在地表的旧玩具、破损衣物,在诅咒的牵引下自动聚集,灵魂能量被污染成暗紫色,即便尚未坠入地底,也已成为随时可能引爆的“定时炸弹”。
48小时后,地表彻底沦陷。核心城市变成了寂静的废墟,只有变异体的嘶吼在空荡的街道间回荡;偏远小镇的幸存者躲在地下室里,靠着仅剩的食物苟延残喘,却不知道诅咒早已顺着通风管道悄然渗透。少数带着微弱决心的人类朝着伊波特山逃亡,他们听说那座山能吞噬一切生命,却不知道这是唯一能暂时避开地表诅咒的“牢笼”。当最后一名逃亡者踉跄着踏入山壁的洞穴,脚下的岩石突然崩塌,他带着满身的诅咒气息坠入黑暗——地底世界的围城,就此拉开序幕。
坠落者的躯体砸在废墟的花丛中,黑色的病毒顺着泥土快速蔓延,最先异变的是回音花。原本流转着轻柔声线的花瓣褪去鲜活,蒙上一层灰败的浊色,茎秆爬满墨黑纹路,细碎的黑雾从花蕊中逸出,随风飘向走廊深处。Toriel正守在遗迹的入口,掌心的火焰突然变得黯淡,眼角渗出细微的黑丝,脑海中涌入无数扭曲的幻境:温馨的小屋被黑雾笼罩,人类孩子的笑声变成尖锐的嘶吼,她下意识握紧手中的火把,意识却在清醒与混沌间反复拉扯——梦魇早已穿透结界,潜入了地底怪物的梦境,精神侵蚀比物理感染来得更快。这位曾放弃王后身份、独自守护遗迹的慈母,此刻正用最后的理智抵抗着精神入侵,她将小屋的门窗用魔法加固,把散落的人类遗物藏进密室,试图为可能到来的幸存者筑起最后一道防线,可指尖的火焰还是渐渐染上了灰黑,那些关于Chara和Asriel的温暖记忆,正被梦魇一点点扭曲成诱捕她沉沦的陷阱。当Frisk顺着遗迹的指引找到她时,Toriel已蜷缩在小屋角落,指尖的黑炎灼烧着地面,却始终没舍得伤害任何生命。“孩子……快逃……”她声音沙哑,眼窝中翻涌着黑雾,仍用最后一丝理智将Frisk推向通往雪镇的大门,自己转身挡住追来的感染怪物,掌心黑炎爆发,与变异体一同坠入黑暗走廊。最终诅咒被压制时,她从黑暗中缓缓走出,浑身虚弱不堪,金色毛发上残留着淡黑印记,过往的记忆变得模糊,只记得自己要守护遗迹,却想不起守护的意义,面对Asgore时,只剩陌生的疏离与莫名的隐痛。
当Frisk顺着藤蔓滑下洞穴,红色的决心灵魂刚触及地底的空气,便骤然悸动起来。她是地表仅存的少数幸存者,为躲避变异体的追杀才闯入伊波特山,此刻灵魂轮廓外已缠上几缕黑雾,指尖触到的岩石都带着刺骨的阴冷。Frisk的决心是对抗诅咒的唯一希望,梦境中被病毒入侵时,她能靠决心凝聚防御屏障,保持部分清醒;物理接触感染者后,身体虽会意识模糊,却能通过存档重生重置状态,清除初期感染痕迹。可击杀变异体时触发的强制感染,还是让她数次陷入自我对抗,灵魂被黑雾缠绕,却始终靠着“救赎地底”的执念保留自主意识。诅咒全域记忆抹除时,她也未完全失忆,地表死者的面容、怪物们挣扎的模样,都化作模糊碎片支撑着她。最终她凭借决心与六魂共鸣,暂时压制梦魇,灵魂上却永远残留着淡黑印记,选择留在地底守护幸存者,时常望着结界方向发呆,清楚知道这场噩梦从未真正结束。
“哟,新鲜的小人类~”Flowey从泥土里钻出来,翠绿花瓣沾着黑尘,往日戏谑的眼神变得空洞麻木,藤蔓猛地绷直,朝Frisk手腕缠去。它本就无魂,全凭决心苟活,地表流入的病毒让它瞬间沦为梦魇的傀儡,凭借对地底的熟悉,借助读取存档的能力预判未感染者行踪,帮梦魇快速扩散灾难,还主动缠上六魂容器,协助诅咒绑定灵魂能量。诅咒被压制时,黑雾从它体内强行抽出,翠绿花瓣恢复原貌,却失去所有力量,瘫在泥土里动弹不得,过往的记忆混乱破碎,既记不起自己是Asriel,也忘了梦魇的操控,只本能地蜷缩着,对周遭一切充满警惕,偶尔会对着六魂容器的方向发呆,眼底闪过一丝莫名的怅然。
雪镇的冰封世界率先迎来浩劫。地表携带病毒的水流顺着岩缝渗入,冻结成墨色的雪花,落在地面便化作细碎的黑尘,覆盖了原本洁白的雪原。流浪猫缩在巷弄角落,琥珀色的眼眸里闪过一瞬诡异的暗芒,转身消失在雾霭中——梦魇已依附在这只猫型生物身上,默默观察着地底的一切。它穿梭于地表与地底,潜入怪物梦境散播病毒,操控Flowey绑定六魂,篡改结界规则,试图突破屏障扩散诅咒。最终被Frisk与六魂的共鸣反噬,无法被消灭的它只能缩成一团黑雾,钻进结界缝隙蛰伏,偶尔会借着流浪猫的形态现身,远远望着地底的幸存者,眼底翻涌着不甘的黑雾,暗中积蓄力量,计划着下一次复苏,甚至开始窥探多元宇宙的其他AU,妄图将诅咒蔓延至更广阔的领域。
Sans靠在路灯旁,标志性的笑容彻底消失,左眼蓝色火焰忽明忽暗,强烈的感知力让他最先察觉诅咒降临,却无力阻止灾难扩散。他看着弟弟Papyrus被梦境病毒感染,挥舞着骨刺,围巾沾着黑渍,眼窝中翻涌着黑雾,从单纯热情的骷髅变成只会追逐目标的变异体,甚至朝着自己发起攻击,内心满是痛苦却始终下不了手。他试图用重力魔法封门、冻结时间、召唤GB炮抵抗,可诅咒早已渗透空间与魔法,能力效果大幅削弱,炮口还渐渐沾染上黑丝。战斗中他数次濒临感染,靠着谨慎与微弱的灵魂韧性勉强支撑,却也因长期对抗变得极度疲惫。诅咒被压制后,Papyrus恢复神智,却失去了灾难相关的记忆,依旧热情地邀请Frisk做朋友,Sans看着弟弟懵懂的模样,没有戳破过往,只是笑容里多了几分沉重,时常独自站在结界边缘,左眼火焰轻跳,警惕着梦魇的动向,默默守护着雪镇的幸存者。
Papyrus的单纯让他毫无抵抗地被梦境病毒侵入,很快沦为变异体,意识与其他感染者连通,朝着同类疯狂攻击,哪怕被击碎骨骼,断肢也能重新拼接,感受不到丝毫疼痛。他的骨刺成了杀戮工具,却在潜意识里残留着对Sans和人类的在意,攻击时会下意识收力,偶尔还会发出残存着挣扎的嘶吼。诅咒被压制后,他恢复了原本的模样,黑渍从围巾上褪去,眼窝中的黑雾消散,却完全忘了自己被感染的经历,依旧执着于抓人类、加入皇家卫队,只是看到破碎的雪镇时,会莫名感到心慌,看到Sans疲惫的神情,会主动提出帮忙巡逻,笨拙地想要守护身边的人。
Grillby酒馆的火焰变成诡异黑炎,Grillby自身也被病毒感染,原本温暖的火焰化作吞噬一切的黑炎,失去了自主意识,沦为只会攻击的变异体,在雪镇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荡,所过之处冰雪都被染成灰黑。最终诅咒被压制时,他恢复了神智,黑炎变回原本的暖橙色,却因能量耗损变得虚弱,酒馆早已沦为废墟,他只能守在废墟旁,沉默地看着往来的幸存者,偶尔会为路过的Sans递上一杯温热的酒,眼底满是茫然与怅然,记不起灾难的细节,只记得曾经有很多怪物在这里欢聚。
往瀑布去的路上,灾难愈发严重。地表流入的垃圾堆积在水域中,黑色的病毒污染了水流,鱼虾变成了带毒的变异体,顺着河道扩散。Undyne浑身是伤,铠甲布满裂痕,长矛魔法光芒日渐黯淡,她有着怪物中罕见的决心,本是抵抗诅咒最顽强的防线,却还是没能逃过感染。她在清醒与混沌间反复挣扎,嘶吼着冲向感染的鱼人,用长矛刺穿变异体的躯体,即便对方断体重生也绝不退缩,最终为了掩护Frisk逃离,主动挡住追来的感染者,被黑色血液溅到,彻底沦为狂暴的变异体,鱼人形态结合诅咒变异,破坏力翻倍,成为瀑布区域的恐怖统治者。诅咒被压制后,她恢复神智,身上的伤口尚未愈合,铠甲依旧残破,却记不起自己对抗变异体的经历,只是看到瀑布的水域时会莫名感到烦躁,看到Alphys时,会下意识挡在她身前,本能地想要保护这位朋友,依旧保持着爽朗暴躁的性格,却偶尔会在深夜惊醒,眼底闪过一丝莫名的恐惧。
Alphys躲在真实验室的防护舱内,看着屏幕上六魂的能量曲线被黑雾扭曲,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,却连诅咒的本质都无法解析。她制造的防御装置被感染反控,Mettaton也沦为变异体,让她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崩溃。她一边躲在实验室里研究对抗诅咒的方法,一边通过监控关注着地底的灾情,内心满是恐惧却始终没放弃希望。当发现Frisk的决心能与六魂共鸣时,她看到了救赎的可能,鼓起勇气将这一发现告知Frisk,为最终压制诅咒提供了关键线索。灾难结束后,她依旧守在真实验室,修复着破损的仪器,只是不再执着于制造机器人,偶尔会和Undyne一起在瀑布散步,看着恢复清澈的水流,眼底渐渐多了几分平静,却始终对那场灾难残留着模糊的恐惧,不敢轻易提及实验室里的过往。
Mettaton被诅咒感染后,无需充电即可永续运转,闪烁着猩红的眼眸,无差别地破坏着热域的一切,原本用于表演的武器变成了收割生命的利器,在工厂与街道间游荡,机械躯体即便被击碎,也能快速拼接重组,成为热域最恐怖的变异体之一。诅咒被压制后,它恢复了神智,猩红眼眸变回原本的颜色,机械躯体布满划痕,却记不起自己失控破坏的经历,依旧执着于表演与热度,只是看到残破的工厂时,会莫名感到失落,偶尔会邀请Frisk和Alphys来看自己的小型演出,试图用热闹掩盖内心的茫然。
热域的工厂里,Burgerpants最早察觉到机械失控,想要逃离却被感染的Mettaton堵住,侥幸躲进仓库才逃过一劫。他胆小懦弱,全程躲在隐蔽角落苟活,看着熟悉的同事沦为变异体,内心满是恐惧却不敢反抗,只能靠着仓库里残留的食物勉强维持生命。灾难结束后,他从仓库里走出,看着残破的工厂与热域,依旧一副颓废的模样,却比以往多了几分劫后余生的庆幸,重新找了份简单的工作,偶尔会向其他幸存者吐槽当下的生活,却绝口不提灾难中的经历,仿佛只要不说,就能忘记曾经的恐惧。
此时的新家王座室,Asgore正守在结界前的六魂容器旁,魁梧的身躯挡在黑雾之前,蓝色斗篷早已被黑色血液染透,红色三叉戟的光芒忽明忽暗。这位地底世界的统治者,性情本就温和不愿伤人,此刻面对诅咒的侵袭,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六魂这最后一丝希望。感染的怪物源源不断地涌入王座室,Asgore挥舞着三叉戟,每一次攻击都能击碎一片变异体,可那些残骸落地后很快就会重新拼接,黑色的病毒顺着伤口渗入他的躯体,金色的毛发渐渐变得灰败,眼角爬满墨黑纹路。他的防御力本就因内心的愧疚而趋近负数,面对不死的变异体根本无力持久,只能靠着首领怪物的悠长寿命强行支撑,脑海中不断闪过Toriel的脸庞、Asriel的笑容,这份执念让他暂时抵抗住了精神侵蚀,却挡不住身体被一点点吞噬。当Flowey带着浓黑雾气缠上六魂容器时,Asgore猛地转身,三叉戟刺穿了Flowey的花瓣,黑雾却顺着武器快速蔓延,瞬间缠上了他的手臂,意识彻底陷入混沌前,他用尽最后力气将三叉戟插在容器前,筑起一道微弱的魔法屏障。诅咒被压制后,他恢复神智,金色毛发上的灰败褪去,却依旧虚弱不堪,看着手中断裂的三叉戟,再看到不远处的Toriel,眼神空洞,两人之间没有交流,只剩沉默的疏离,他放弃了王座,选择留在新家的废墟旁,偶尔会打理周围的花草,眼底满是茫然,记不起自己守护六魂的经历,也忘了与Toriel的过往纠葛,只觉得内心空落落的,仿佛丢失了很重要的东西。
六个人类灵魂被诅咒强行绑定,能量被污染成暗紫色,原本的光操控、时间操控等能力被扭曲,沦为诅咒扩散的能量源,逸散出的能量化作诅咒光束,接触者会瞬间被感染。它们无法被直接腐蚀,却因无自主宿主,只能被动承受梦魇的操控,成为其突破结界的关键。最终在Frisk的决心共鸣下,附着的诅咒能量被强行剥离,恢复了原本的色彩,却依旧残留着淡淡的诅咒印记,重新回到容器中,能量波动变得微弱,偶尔会随着Frisk的决心闪烁,仿佛在回应她的守护,却也成了梦魇复苏的潜在隐患,只要梦魇再次觉醒,依旧可能被重新绑定。
怪物小孩在瀑布玩耍时,吸入了回音花散播的病毒,很快被感染,沦为变异体,跟随着Undyne的脚步,朝着未感染者发起攻击,小小的身躯即便被撞倒,也能快速爬起,感受不到疼痛。诅咒被压制后,他恢复神智,回到了瀑布的角落,依旧喜欢躲在岩石后观察路过的人,却忘了自己被感染的经历,只是看到Undyne时会格外亲近,偶尔会问起为什么瀑布的水流曾经是黑色的,得到的却只有Undyne沉默的摇头。
河流人坐在瀑布的河道旁,很快被污染的水流感染,失去了自主意识,不再哼唱熟悉的歌谣,只是漫无目的地坐在岸边,偶尔会朝着路过的生物伸出手,指尖滴落的黑色液体带着病毒。诅咒被压制后,他恢复神智,重新抱起琴,却再也弹不出完整的旋律,看着清澈的水流,眼底满是茫然,记不起自己曾经被感染,只是觉得内心很空,偶尔会对着河道的方向发呆,仿佛在等待什么。
危机暂时解除,可地底早已残破不堪,怪物数量锐减至原本的5%,死亡的变异体尽数消失,只留下一片狼藉。幸存者们失去了关于灾难的记忆,茫然地看着破碎的家园,只残留着莫名的恐惧。雪镇的黑雪停了,瀑布的水流复归清澈,热域的机械恢复运转,可地底的每一处角落,都残留着诅咒的痕迹,结界缝隙中,梦魇的黑雾仍在悄然蛰伏,这场未完结的灾难,终究只是暂时落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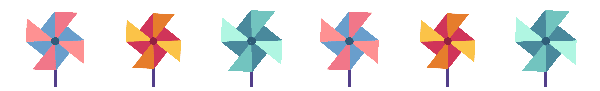
声明:该文章由ai生产
详细记载请去看另一个作品《梦中传说》